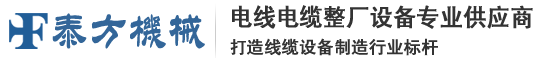產業創新由“工(gōng)程師時代”進入“科學家時代”。以科(kē)技創新引領束絲機產業創新,是世界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大趨勢,對於我國(guó)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而言有著重要現實意義。
近日,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推動中部(bù)地區崛起座談會上指出,“要以科技創新引領產業創新,積極培育和發展新質(zhì)生產力”,為中部地區培(péi)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指明了方向。當今世界,產(chǎn)業創新早已由“工程師時代”進入“科學家時代”。以科技創(chuàng)新引領產業創新,既是世界(jiè)科技革命與(yǔ)產業變革(gé)的大趨勢,也是我國加快發展新質生(shēng)產力的內在要(yào)求。
產業創新早已進入“科(kē)學家時代”
在(zài)1912年出(chū)版的經濟發展理論(lùn)中,熊彼特將創(chuàng)新首次引入經濟學,並將其定義為“建立一種(zhǒng)新的生產函數”,主要包括五種(zhǒng)情況,即引進新產品、引(yǐn)用新技術、開辟新市場、控製原材料的新供應來源以及實現企業(yè)的新組織。科技創新與產業(yè)創新二者在內涵與(yǔ)外延上存在很大的(de)交叉。如果做(zuò)個(gè)簡單區分,科技創(chuàng)新側重指科學新發現(xiàn)和新知識(shí)、新技術、新工藝的創造過程,而產業(yè)創新側重指科學(xué)新發(fā)現和新知識、新技術、新工(gōng)藝在產業發展中的應用過程。
人類發展史上,早期的技術創新主要靠實踐(jiàn)中的偶然發現和反(fǎn)複(fù)試錯來(lái)實現。現代社(shè)會(huì),科技創新對產業創新的引領作用(yòng)日益凸顯。一方麵,因為有了科學家發現和(hé)總結的科學(xué)原理做指引,產業創新效率(lǜ)得到(dào)極大的提升,可以大幅減少不必要的試錯。比如(rú),物理學中的香農(nóng)定理,就給無線通信(xìn)產業領域的技術創新和產品設計規定了(le)“航道”。另一方麵,科學家的(de)發現和發明極(jí)大推動了產業創新。比如,華為5G技術及相關(guān)產品,其源頭就是土耳其Erdal Arikan教授的一篇學術論文。當前,科學家集聚的大學和(hé)科研院所已經成(chéng)為產業創新的源頭。2017年4月,美(měi)國知名經濟智(zhì)庫米爾肯研究所評估了超過200家(jiā)美國大學的技術轉讓和商業現狀後(hòu),特別指出:“大學和研究機構,是(shì)培育高科技產業唯一(yī)最重要(yào)的(de)因素”。
科技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內在要(yào)求
新(xīn)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(zuò)用(yòng),由技術革命性(xìng)突破、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、產業深(shēn)度轉型升級而催生的。新質生產力與科技創新、產業(yè)創新三者之間的關係,可(kě)以簡單理解為,科技創新是產業創新的先導,而符合高科技、高效能、高質量特征的產業創(chuàng)新結果就體現(xiàn)為新質生產力。可見(jiàn),科技創新引領作用發揮越充分,產(chǎn)業創新就(jiù)可能更高(gāo)水平、更富效率,新質生產力就更發達、發(fā)展就(jiù)更為(wéi)繁榮。
當前,我國科技(jì)創新對產業創新的引領作用發揮得還不充分,二者之間還存在脫節和“兩張皮”現象,對新質生產力的培育(yù)和發展形成了一定的製約(yuē)。一方麵,我國高水平科技(jì)創新產出還不夠,引領力偏(piān)弱。對於我國產業創新和發展的整體水平,習近平總(zǒng)書記曾做過(guò)判(pàn)斷,認為“我(wǒ)國(guó)關鍵核心技術受製於(yú)人的局麵尚未根本改變,創造新產業、引領未來發展的科技儲備(bèi)遠遠不夠,產業還處於全球價值鏈中低端”。其中,“關鍵核心技術(shù)”“創造新(xīn)產業(yè)、引領未來發展的科技儲備”指的就是高水平的科技創新產(chǎn)出。
另一方麵,我國科技創新成果的轉化率還不高,引領還不暢。根據國家知識產權發布的數據,截至2023年底,我國發明專利有(yǒu)效量為499.1萬件,成為世界上首個國內有效發明專利數量突破400萬件的國家。但盡(jìn)管如此,與發達國家相比(bǐ),我國(guó)科技成果轉化率仍(réng)較(jiào)低(dī),在30%左(zuǒ)右,遠低於發(fā)達國家的60%-70%。大量科技創新成果沒有(yǒu)及時應(yīng)用到產業創新中去,也就沒有轉換為現實的新質生產力。
強化科技創新(xīn)對產業(yè)創新的(de)引領作用
科技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(sù)。在以科技創新引領產業創新方麵下更大功夫,必須更(gèng)加重視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(xīn)的深度融(róng)合,強化企業科(kē)技創新主體地位,促進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(róng)合,推動科技成果加快轉化為(wéi)現實生產力。
加強(qiáng)重大科技攻關,增(zēng)強產業創新發(fā)展的技術支撐能力。關鍵核心技術是(shì)要不(bú)來、買不來、討不(bú)來(lái)的。針對我國產業(yè)發展領域的諸(zhū)多“卡脖子”技術,尤其是大型複雜裝備技術,須(xū)構建科技創(chuàng)新新型舉國體製,開展重大科技攻關。以鐵建重工盾構(gòu)機研發為例,國家發起和推動(dòng)的重大科技攻關計劃(huá)功不可沒(méi)。早在2002年(nián)8月(yuè),科技部將“直徑6.3米全(quán)斷麵隧道掘進機研(yán)究計劃”列入863計劃(huá),通過國家項目資助的形式提供資金要素,培育(yù)了一批人才(cái),儲備了盾構機技術研發的原理性知識,也為後期企業市場驅動的技術商業應用與(yǔ)競爭打下了堅實基礎。
強化企(qǐ)業創新主體地位,構建上下遊緊密合作的創新聯合體。習近平總書(shū)記指出,“更加重視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深(shēn)度融合”。二者深度融合的具體方式有兩種,其中一種就是產學研用協(xié)同創新。2012年,為攻克前沿產品全斷麵硬岩隧(suì)道掘進機的關鍵技術,鐵建重工上遊聯合了供應商與科研院所開展相(xiàng)關技術原理的攻關,下遊聯合中鐵十(shí)八局等施工單位進行產品的驗證與反饋,鐵建重工則作(zuò)為集成商負責整體方(fāng)案的設計(jì)與產品(pǐn)的集成總裝,構建一個上下遊緊密合作、產學研用閉環的創新聯合體。該創新聯合體用不到3年時(shí)間,就成功(gōng)突破了核(hé)心技術,國產首台敞開式全斷麵硬岩隧道掘進機成功下線(xiàn)。
積極引進國內外一流研發(fā)機構,推動研發企(qǐ)業(yè)(中心)高密度集聚。科技創新和(hé)產業創(chuàng)新深度融合(hé)的另外一種(zhǒng)方(fāng)式,就是大力發(fā)展研(yán)發企(qǐ)業(中(zhōng)心)。在科技創新到產業創新的全鏈條中,研發企業(中心)的(de)功能與作用十分關鍵。一方(fāng)麵,他們和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完成創(chuàng)新的“從0到1”;另一方麵,又與(yǔ)製造企業協作實現創新的“從1到100”。從世界科技創新的格局看,歐美發達國(guó)家在創新的“0到1”上具有比較優勢,而中國則在“1到100”上具有顯著優勢。2023年6月,湖南省委提(tí)出將長沙(shā)打造成為全(quán)球研(yán)發中心城市,其重要意義就是將歐美發(fā)達(dá)國家以及國內先進城市在“0到1”上的優勢,與先(xiān)進製造(zào)業發達的長沙乃至湖(hú)南在“1到100”上具備的優勢實現對接(jiē)交匯。
統籌推(tuī)進深(shēn)層次改革和高水平開放,為科技創(chuàng)新引領產業創新提供環境與製(zhì)度(dù)支撐。要針對科技創新到產業創新全過程各個環(huán)節,推(tuī)進深層次改革和體製機製(zhì)創新。比如,針對教育、人才培養與科(kē)技創新的脫節問題,就須深化教育、科技、人才綜合改革(gé),統(tǒng)籌推動教(jiāo)育、科技、人才(cái)一體化發展。比如,針對當前科研(yán)成(chéng)果(guǒ)專利轉讓費用普遍偏高(gāo)問題,可以探索構建新型科研(yán)成果產權收益製度,降低科研成果專利轉讓門檻(kǎn)。針對(duì)當前科(kē)研成果轉(zhuǎn)化成功(gōng)率普遍偏低問題,可以探索(suǒ)培育壯大科技企業家群體的方式與路(lù)徑,有力化解科研成果轉化過程中存在的“找不到”“談不攏”“難落地(dì)”等現實(shí)問題(tí)。此外,還要持續打造市場化、法治(zhì)化、國際(jì)化(huà)營商(shāng)環境,為創新創業提(tí)供一(yī)流的環境保障。